|
【内容提要】在中国早期画像艺术中对“空间”的视觉表现之变迁历程中,东汉晚期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画像艺术中对“空间”的视觉表现上出现了一个较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也直接促成了隋唐时期中国古代绘画艺术中对“空间”表现模式的成熟。这种“变化”应该是与东汉晚期以来,当时士大夫画家阶层在绘画理论构想与绘画实践活动上,对这一问题进行独特的关注分不开的。 【关 键 词】古代中国/早期画像艺术/空间表现/变化/原因 【作者简介】刘晓达,广东教育学院美术系教师。(广州 510303) 中图分类号:J23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8754(2008)04-0097-08 一、问题的提出 在中国美术史研究中,画家或画工阶层在平面上对纵深“空间”的塑造,应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课题。在历史上,有关的学者也曾就此问题进行过颇多的讨论。比如,北宋中期的画家兼理论家——郭熙在《林泉高致集》中,即以山水画的创作为例,对此进行了一些理论上的探讨。而他所提出的那著名的关于山水画“空间”表现的“三远”(高远、深远、平远)理论也一直为后人所称道。而稍后大约在北宋末期生活的另一位画家——韩拙所提出所谓的“阔远、迷远、幽远”等理论则显然系对郭熙“三远”理论的继承与发展[1]。及至近代,有关的学者像宗白华、阮璞等先生也对此做了进一步的关注。比如,美学家宗白华先生主要是通过美学思辨对比了中、西绘画艺术中对空间塑造的视觉差异性,并提出:与西方绘画中运用科学与严谨的焦点透视方法真实地表现自然万物的空间观念相比,中国古代的绘画中对空间的表现实际上是一种“折高折远自有妙理”的散点透视方法。按照作者的理解,这是一种把握着大自然的节奏与和谐,流瞥上下四方、一目千里、把握全境的阴阳开阖、高下起伏的节奏的方法[2]。而美术史家阮璞先生则娴熟地运用丰富的古代画论及诗文知识对此进行了反驳,指出其差异性并非那么巨大。[3]应该说,两位学者在关于中、西方绘画中,对“空间”表现差异问题的讨论,对于我们继续研究这个学术问题奠定了初步的理论基础。但笔者窃以为:二位先生在讨论到中国早期绘画艺术中的“空间”塑造问题时,似乎还显得不太全面、系统与深入。比如说,两位学者虽然注意到中、西方绘画艺术中对“空间”表现的差异性,但是,就中国本身的画像艺术而言,在历史上其对“空间”的视觉表现历程到底是怎么演变的?两位学者似乎并未就此讨论清楚。况且,以笔者看来,他们在研究“中国古代绘画中对‘空间’进行的塑造”这个有意思的议题时,大都还是运用了魏、晋以来的诗文或画论文献材料用以支持他们的观点。但是,考虑到早期中国画像艺术材料在形式上的复杂状况,我们在对“空间”问题进行讨论时,如果单纯依赖文献资料来对这个问题进行理解,那么,我们似乎并不能够把有关的问题说得清晰、透彻。 此外,现在的美术史学界也已经普遍认为:及至北宋中、晚期,中国古代的画家和画工群体,在对纵深“空间”的塑造上已经趋于成熟。从晚唐、五代时期的荆浩、关仝、董源、巨然,再到北宋时期擅写全景山水的范宽、李成、燕文贵、郭熙,这些画家群体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已经较为娴熟地懂得运用如何在平面上去展现纵深的空间。所以在北宋中期,郭熙提出他那著名的“三远”理论也并非是空穴来风,应该有其深厚的艺术与社会文化基础。①在笔者看来,一种视觉艺术表现观念的形成与成熟,应该有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北宋中、晚期的艺术家群体所达到的对纵深式“空间”的艺术表现水平,应该是与前代画工和画家群体的不断探索息息相关的。假如我们能够把中国古代画家与画工群体对“空间”的表现这一独特的历史过程进行恰当的“复原”,并进而概括出其若干发展规律。那么,我们或许就能够对这个课题有一个更为客观、深入与通达的理解。而如果我们要对此课题展开深入的解读,离开画像艺术本身而空谈文献是不能够把一些问题解释清楚的。因此,笔者在该文中,即希望于通过对早期中国时期的画像资料与文献材料进行系统与综合性的梳理,来对该问题进行更为细致与深入的阐释。 二、中国早期画像艺术中对“空间”的塑造过程 由于早期(先秦—隋唐)的画像材料在对“空间”的表现上较为复杂,也多有变化。因此在下文中,我希望能够以一种历时性的笔法,分两个时段将早期中国各时期的画像中对空间的塑造进行客观的阐述与解释。 1.旧有的传统:先秦—西汉时期 从目前已出土的画像材料上看,在对“空间”的表现上,自先秦以来就始终就存在着一种特别的风格。即在画面中,画工往往会采取一种“上、下分层”式的方法,将画像按一定的“分层”原则依次画出。而其刻画的主要人物形象则往往被描绘为全侧面或四分之三侧面,而这些人物也多是处于行动的状态中,有点类似于现在我们说到的“剪影”。通过这一图像处理,进而展现人物在特定“空间”中的行为、举止。这一表现特点,也被一些学者如巫鸿先生称之为自先秦时代,即已形成的所谓“情节式”的构图范畴。[4]比如,出土于四川成都百花潭地区的宴乐渔猎攻战纹壶纹样(战国时期),就是遵循着这一表现方式。在该画面上,画工把采桑、射猎、饮宴、水陆攻战等在不同的历史时段发生的情节按照“上、下分层”式的构图规则依次布列,虽然这种表现手法并不符合我们现在所认同的那种对“空间”的塑造原则,但该幅画面仍然向我们展示了先秦时代的画工群体对“空间”所进行的独特处理。尤其是,对于该幅画面的第二层右边展现饮宴、歌舞的场面表现上,考古学家刘敦愿先生就认为这种上、下式的构图其实也是体现了一种纵深的空间意识。如他所言:“在这种情况下,物象纷然杂陈场景,如需区别层次,必然要以物象的上、下位置来表示远近关系。例如:宴乐场面中,华屋之下,宾主杯觥交错,表示尊者、贵者的酬应在上;堂下的悬钟与磐,表示乐工的演奏在下——观者先见乐工演奏,后见宾主饮宴。因此,在下者就是在前,在上者也就是在后。”[5]应该说,刘先生的观点是较为合理的。在先秦时期的古代中国画工们,尚未摸索出一条系统性的展现空间的意识之前,这种以“上、下式”布局来展现空间的办法应该也不失为一种独特的塑造方式。只不过,笔者认为这种塑造“空间”的表现手法与我们现代人的认知观念有所不同罢了。(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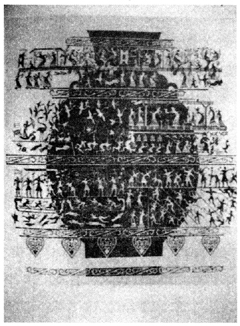 图1战国时期宴乐渔猎攻战纹壶 (图片来源:田自秉、吴淑生编:《中国工艺美术史图录》(上),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第262页,图260) 到了西汉时期,这种按照“上、下分层”式的构图规则来展现“空间”的意识仍然能够清晰地看到。比较著名的例子当然就是上个世纪70年代,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中出土的那段“T”字型帛画。在这段著名的帛画作品中,画工将该帛画的内容分为天上世界、人间世界、地下世界三个画像思想主题分别加以表现,显示出画工集团秉承着墓主家人的信仰思想,对宇宙-空间观念所进行的独特的思想构思。此外,该幅画像中、下层中,对墓主轪侯夫人及其侍从,以及祭祀场面的描绘也颇值得我们加以细致的关注。该幅画像中层中对轪侯夫人及其侍从的表现倒是延续了先秦以来的通过“全侧面”式的表现来展现特定的空间的传统。但是该幅帛画下层中对祭祀场景的表现,却也揭示出艺术工匠另一种独特的对“空间”的塑造。在这一场景中,画工把用来做祭祀的鼎、壶等礼器叠放在最前端。而在其后部则依次展现了祭祀中的人物及用来设祭的菜肴、馔品。这样一种表现形式,就把原本属于不同事物的三组形象依次放入进一种纵深式的空间中。虽然这一表现场景并没有被描绘在该幅帛画中最显要的位置上。但是,我们还是能够注意到此一时期的画工对“空间”问题的独特关注。而从这一特殊的表现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即便是在一种已经约定俗成的“上、下层”式的空间构图规律中,中国早期的艺术工匠仍然能够在此基础上再寻求一些细节上的变化,以获得新的视觉空间的表现观念。(图2)  图2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帛画(覆盖在墓主内棺上) (图片来源:湖南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下集,1973年10月,第49页,图七一、第59页,图七六、第61页,图七七) 2.新“变化”的出现及确立:东汉中、晚期—隋唐时期 进入东汉以后,渊源自中国传统艺术中的那种按照“上、下分层”式的构图规则来展现“空间”的风格依然存在,而且还较为普遍。譬如,东汉中、晚期在山东嘉祥县由当地的武氏家族修建的武梁祠堂中,画工仍然按照传统的“上、下分层”式的构图规律去展现不同的空间。例如在该祠堂西壁画面上之第三层中,在表现车马出行的场景时,为了展现远处的人物与近处人物的空间关系,修建该祠堂的画工就索性将其叠放近处的人物之上,希望借此来表现远近的空间关系。②而这种表现手法,也可以说是对先秦以来古代画工群体对“空间”进行传统式表现的延续。(图3)  图3山东嘉祥武梁祠西壁画像 (图片来源:中国画像石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画像石全集1·山东汉画像石》,山东美术出版社、河南美术出版社,2000年,第29页,图49) 然而,我们同时也注意到:东汉中期以后的一些画像材料对空间的表现,却已开始显现出某些新的变化。总体说来,在东汉中、晚期,在山东、河南、陕北、四川以及内蒙古等地区修建的壁画墓或画像石墓中,画工对举凡“宴饮、拜谒、议事、庖厨、乐舞百戏、楼阁庭院”等场景的描绘都开始采取一种“俯瞰”式的视角去表现。而这些对空间塑造的新的变化特征,目前在山东诸城市前凉台、沂南北寨、费县垛庄潘家疃、河南密县打虎亭、河北安平、陕北绥德县延家岔、四川成都羊子山、乐山,以及内蒙古和林格尔等地出土的画像石、壁画墓中也均有发现。这一时期的画工通过这种表现手法,试图将日常人物的诸多活动较自然的放置进楼阁、庭院、长廊等较大的立体式建筑空间中,并进而展现一种纵深的“空间”。比如,在山东沂南北寨东汉画像石墓室中出土的一幅楼阁庭院图中,画工即以“俯瞰”式的构图视角,试图将东汉晚期人们居住的庭院内的诸多场景都作一一展现。只不过,由于此一时期的画工依然未能较好地处理人物与建筑之间的比例协调关系,因此在该幅画像中,我们也可以清晰地看到:画工在此一时期对人物的塑造依然显得过大,而对画面中纵深式建筑的表现又显得过于狭小。人物与楼阁等建筑空间的关系还未能处理的足够周详。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当一种新的视觉表现图式出现时,它往往要历经数代画工或画家群体的不断探索方能完全取得成熟。(图4)  图4山东沂南北寨汉墓中室南壁横额西段画像·楼阁图 (图片来源:中国画像石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画像石全集1·山东汉画像石》,山东美术出版社、河南美术出版社,2000年,第154页,图二0五) 而这种对“空间”塑造上的新的视觉表现变化,我们实际上在其后南、北朝时代的画像材料中也能看到某种延续性。对此,苏立文先生曾经正确指出:“整个6世纪的艺术中,人物画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但由于对自然景观描摹的技术问题已被解决,山水背景越来越突出。”[6]而山水画作在此一时期的出现,也的确预示着古代中国的艺术家阶层,开始凭借此画种对“空间”问题进行更一步的关注。实际上也的确如此,在洛阳附近出土的北魏晚期的宁懋石室、孝子石棺、元谧石棺等画像中,我们注意到当时的一批出色的画工已经能够娴熟地将反映儒家伦理道德观念的“孝子”画像主题,融汇进极具纵深空间效果的山水画主题中。例如,在洛阳出土的一套制作于北魏时期的“孝子”题材的画像石棺中,画工就以“俯瞰”式的视角,将两汉时期儒家文化中一些孝子的形象放置进疏密有致的林木之中,并将对人物的描绘与他们所处的客观环境自然的协调在一起。从图像上我们也可以清晰地看到:在该幅作品中,人物与建筑之间的比例关系已经基本准确,并共同依存于山林这一更为深邃而幽远的未知空间中。画工在描绘这些人物与山水景观时,实际上也依然延续了自东汉晚期以来就已渐次出现的、通过“俯瞰”式的视角去表现纵深“空间”的意识。(图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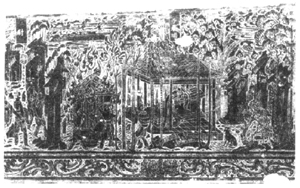 图5洛阳出土北魏时期创作的孝子石棺床·孝子蔡顺 (图片来源:中国画像石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画像石全集8·石刻线画》,山东美术出版社、河南美术出版社,2000年,第40页,图五三) 而在古代中国美术发展史上,通过在卷轴画卷上表现纵深“空间”的意识,可以作为成熟标志点的画作,应该就是以传为隋代展子虔所作的《游春图》作为肇始点的。关于《游春图》作者的身份及其准确的创作年代虽然还未能最终确定,③但将其定为隋、唐初期(公元6世纪末—7世纪初)是大致没有什么问题的。(见图6)该画卷的描绘大体上是延续了洛阳附近出土的北朝时期石棺画的风格传统。与前者不同的是,该画的创作事实上已经将山水画作为一种独立的画种,而不再依附于人物画的背景中。艺术家所运用之视角则大体延续了东汉晚期以来渐趋形成的“俯瞰”式表现方法:前景是一片坡坨与树林,中、右景则由一大片开阔的湖面来展现辽阔的空间,位于画面之右上角则是表现了若隐若现的层峦叠嶂的山峰。而在该画卷中,无论是山川、湖泊、舟船、人物,其比例关系已经趋于准确。尤其是,对舟船、人物的具体刻画已经完全服从于画面的整体构图之中,在此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在这幅画面中,对人物的描绘也不再像前文中曾指出的、在洛阳附近出土的北魏晚期画像石棺中的“孝子”题材那样成为视觉的中心,而是完全退居次席,成为辽阔而幽深湖面上一个小小的点缀,而画家这样做的目的,也无疑是希望将所有的物象要素全部融汇入一个整体而纵深式的“空间”中。可以说,《游春图》的创制完成揭示了一个在此后三四百年中,古代中国画家塑造空间关系的规则。这个“规则”或许就是:通过“俯瞰”式的视角去细致地描绘真实的自然,并且在这一客观表现过程中,尽可能地营造出纵深的“空间”意识。而这一表现特点,我们在观察其后在创制年代上,大体已确定在中唐时期的《江帆楼阁图》(图7),以及同一时期甘肃敦煌唐窟中的诸多经变画像题材中都能够清晰地看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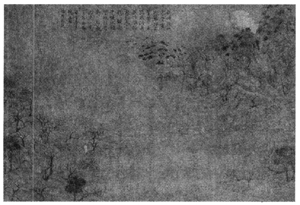 图6传为隋·展子虔创作的《游春图》 (图片来源:中国美术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美术全集·绘画编·隋唐五代绘画2》,人民美术出版社,1984年,第1-5页。) 《江帆楼阁图》的构图方式与《游春图》略有不同:这幅画卷的近景处主要是展现了在崇山郁岭的掩映下,一群旅人正在悠闲地前行,他们或骑马、或散步。在他们行进的前方,一排排的楼阁、长廊等建筑则掩映在密林深处。在这一部分中,楼阁、长廊等建筑在比例上,已和处于它外层的那些树林非常协调。而在峻峭的连绵山岭外侧,辽阔的江岸上则点缀着几许孤帆,这种处理手法亦进一步地增强了画面的空间感。而整个画面也处在一种均衡与自然的布局中。虽然画家在此处对山岭、江面的笔墨技法之描绘、处理与前所提到的《游春图》的表现手法有所不同,但在笔者看来,就整体性的表现方法来说,这幅画面所展示的“空间”表现意识却依然属于一种“俯瞰”式的构图格局,画家是从他描绘客观物象的高处将他所看到的景象一一做了细致的布置与表现。而从这幅画面上,我们也能够自然地将其与自东汉晚叶以来就已开始出现的、对“空间”的新视觉表现特征连缀起来。只不过,与东汉、南北朝时期的画像中对“空间”的新视觉表现相比,这幅画面所表现出的对“空间”的塑造意识与效果已经完全趋于成熟。而在以上的讨论中,笔者所指出的自东汉晚期以来,中国早期画像艺术中对“空间”的表现所反映出来的这一有趣的“变化”现象,实际上也是值得我们认真加以考虑的。  图7传为(唐)李思训创作的《江帆楼阁图》 (图片来源:徐邦达主编:《中国绘画史图录》(上),第26页,图一五) 三、问题的延伸 以上,我们大体上以历史性的维度,对先秦以来古代画像材料中对“空间”的表现之“变化”历程做了大致的勾勒。而从上文的客观叙述中,我们实际上已经可以从这一现象中得出一个较为清晰的结论。这对于我们正确理解自先秦以来,古代中国的画工群体对“空间”的视觉表现规律是有一定的意义的: 第一,从先秦以来,古代的画工集团已经开始着眼于对空间的视觉表现,但早期艺术中,对“空间”的表现主要还是通过采取一种“上、下分层”式的构图方法,将画像题材按一定的“上、下分层”式的原则依次画出。而其刻画的主要人物形象则往往被描绘为全侧面或四分之三侧面,而这些人物也多是处于行动的状态中,有点类似于现在我们说到的“剪影画”。通过这一图像处理,画工可以进而展现人物在这一特定的“空间”中所表现出的行为、举止、情节。 第二,大概从东汉中、晚期开始,古代中国的艺术工匠集团开始试图对“空间”的表现进行一定程度上的“视觉”革新。具体的表现方法是:通过采取一种“俯瞰”式的视角模式,将举凡人物、建筑、山水等自然物象,按照较为妥帖的“比例”规则,共同融汇进一种纵深的“空间”中。当然,就目前现存的早期画像资料看,从东汉晚期—南北朝时期的画像材料中,早期画工们对“空间”处理的新视觉表现明显要稚嫩一些,而到了南北朝晚期—隋唐时代,这种通过“俯瞰”式的视角模式对“空间”进行表现的新视觉图式已经逐渐趋向于“定型”。而这种表现模式,在五代、北宋时期也终于走向全面的成熟。 从刚才的总结中,我们实际上已经能够看出:东汉晚期—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早期画像艺术中对“空间”表现的一个重要“分水岭”。在这一分水岭的前后,古代中国画像艺术中对“空间”的表现实际上是大异其趣的。但是,这也就自然的显现出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为什么这种“变化”会出现在东汉晚期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换句话说,是什么原因促使了这样一种对“空间”的视觉表现变化?在笔者看来,促使这一变化的原因当然会有多种。但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或许就是:自东汉晚期以来,士大夫画家的崛起及所伴随而来的对塑造“空间”的议题所进行的全新思考与视觉的表现,对这一“变化”的促成应该具有一定的影响性。 从目前的绘画史文献中,我们已经可以清晰地看到,在东汉晚期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正是中国第一批士大夫画家真正崛起的时代。据(唐)张彦远《历代名画家记》记载:在东汉晚期,诸如蔡邕、刘褒、赵歧、张衡等士大夫群体大都精于绘事。其中的士大夫画家刘褒更是对诸如《云汉图》、《北风图》这类山水式的题材情有独钟。[7]而在稍后的魏、晋南北朝时代,随着顾恺之、张僧繇、陆探微、杨子华、宗炳、展子虔等人的出现,士大夫画家作为当时中国画坛上一个特殊的群体,更是对当时的中国绘画艺术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他们在那一时代出现的重要意义,就在于他们的艺术创作,对当时的艺术表现观念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这其中,有一些著名的士大夫画家就曾经对如何在画面上展现纵深的“空间”进行了艺术实践或理论上的思考。比如,在东晋晚期,当时著名的士大夫画家顾恺之即在其绘画理论著作《画云台山记》中,就试图对如何塑造山水“空间”的问题而展开了一些初步的理论性构思。在这篇著名的画论文章中,作者主要考虑的是在对云台山这一道教圣地景观的创作上,该如何将其与东汉末期的道教祖师张道陵及其弟子们修炼的场景合理的融汇在一起。比如,在该文中作者除细致勾勒出云台山东段、中段及西段大体的山脉走势、山峰中与崖面、溪流与树林的布列位置之外,还着重说明了在此画面中,张道陵及其弟子们该怎样被放置在群山间的丹崖之上。如文中就曾有如下对山水与人物间关系的细致的描述:“……画丹崖临涧上,当使赫巘隆兴,画险绝之势。天师坐其上,合所坐石及荫。宜涧中,桃傍生石间。画天师瘦形而神气远,据涧指桃,回面谓弟子。弟子中有二人临下,倒身大怖、流汗失色……”短短几句话,就将张天师及其两位弟子与他们所处的空间关系进行了较为明确的说明与交代。[8]遗憾的是,顾恺之的这篇文章只是他对云台山创作的一个构思草稿,据目前的文献信息显示,他在一生中也没有将这篇独特的“构思”转变成为为现实的画卷。而就目前所存的、宋代画家们依据顾恺之原作《洛神赋图》所复制的(宋)摹本看,虽然画面中的山水、树石的景象渐趋增多,对树石、山峰的布列也疏密有致,但画卷中的人物与山水等客观环境之间的比例关系依然很不协调,仍然脱离不了在早期中国山水绘画中曾广泛流行的所谓“或人大于山、或水不容泛”的稚嫩风格。但即便如此,我们从顾恺之的《画云台山记》中,依然可以看出作者为了较好地把握山水题材中人物与客观环境中的比例关系与空间意识而所做的努力。 当然,在南朝宋代初期另一位士大夫画家宗炳在《画山水序》中,也对如何表现纵深的“空间”展开了一些颇有价值的思考。如他在文中就这样写道:“……且夫昆仑之大,瞳子之小,迫目以寸,则其行莫睹。迥以数里,则可围于寸眸。诚由去之稍阔,则其见弥小。今张绡素以远映,则昆阆之形,可围于方寸之内。竖划三寸,当千仞之高。横墨数尺,体百里之迥……”[9]这表明他和东晋晚期的顾恺之一样,也希望在对山水空间的把握上,能够通过眼睛对远方山水景观进行有意识的取舍,从而较好的展现他所谓的“横墨数尺,体百里之迥”的视觉空间效果。除此之外,与顾恺之相比,宗炳在塑造“空间”上的另外一个重要理论发现,就是他注意到在观察与展现纵深空间时,应该始终与他所描绘的景观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样就可以把自然景观融汇于尺幅画卷上,从而达到表现纵深空间的效果。这也就是宗氏所谓的“迥以数里,则可围于寸眸。诚由去之稍阔,则其见弥小。”只不过,由于年代久远,宗氏创作的一系列山水作品也没有遗留下来。因此,我们也无从看到他在具体对“空间”进行表现时的效果到底怎样。而据初唐时期成书的《南史》记载,主要在南朝梁代晚期活动的一位士大夫画家萧贲,其画作也有“会于扇上画山水,咫尺内万里可知”的幻觉风格。[10]这表明在那一时代,士大夫画家萧贲所创造出的这种“会于扇上画山水,咫尺内万里可知”的山水效果已经为时人推崇与接受。而《南史》对此有专门的记载,似乎也表明这种视觉风格在当时应该属于一种比较新颖的表现图式。无独有偶,活跃于北齐——隋代的另一位士大夫画家展子虔,据《历代名画记》记载,其画风更有“触物留情,备皆妙绝,尤善台阁人马,山川咫尺千里”的视觉图式趣味。[11]就像前文笔者已经谈到的,《游春图》虽然在目前还未最终确定是否为展子虔所绘制,但目前美术史与书画鉴定学界也已经普遍把这幅作品定为南北朝晚期或隋唐初期。因此,即便这幅作品不是展子虔所作,它也应该是与展子虔生活在同一时代、在画风上与展氏极为相似与接近的另一位出色的画家所为。 在笔者看来,以上的文献资料实际上都在显示着一个历史事实。也就是说,对如何在平面画面上塑造“空间”这一问题上,东汉晚期以来,逐步在画坛上崭露头角的这一批士大夫画家们的确是在认真地思考,并在绘画实践上努力加以一步步的实现。如果说,顾恺之与宗炳二人只是对如何表现“空间”意识,进行了前期的理论基础构想与初步实践的话,那么,在南北朝晚期活跃在当时画坛上的两位著名士大夫画家——萧贲与展子虔实际上就是在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地将这一理论构想逐步地转换成了一种“视觉现实”。我们从上述的这些文献中,亦能够清晰地看出这一表现手法与观念从刚开始的逐步提出,再到后来慢慢的实现这一“连续性”的历史进程。而这一历史进程,我们在前文中,通过细致的观察东汉晚期以来的画像材料中,对“空间”的视觉塑造变迁中亦能够清晰地看到。 从某种角度上说,在东汉晚期至南北朝时期,通过山水画这一独特的画种来对“空间”进行艺术实践的画家又何止以上的这几位画家?除了前文中我们已经注意到的、在东汉晚期以来已有一些士大夫画家参与到山水画的实践之外。在初唐时期,由裴孝源主持编撰的绘画目录学著作《贞观公私画史》中,也清晰的著录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十多位贵族与士大夫画家群体,诸如戴逵、毛惠秀、梁元帝、杨子华等人绘制的山水作品。[12]而就一般的艺术常识而言,山水画实际上也是一种最能够在二维平面画卷上,去展现纵深“空间”的重要的艺术表现样式。中国自东汉晚期以来的士大夫艺术家们通过选择山水画这一独特的画种去展现“空间”意识,实际上也能够体现出他们的敏锐的视觉判断力与艺术表现力。 四、结论 如果我们把前面所述的诸多画像与文献联系在一起进行考虑,那么,我们应该就会得出以下的一个重要结论:在东汉晚期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早期画像艺术中对“空间”的表现为何会出现一个较大的视觉“变化”?在笔者看来,它应是与当时士大夫画家阶层在平时的视觉理论构想与绘画活动上,对这一问题的独特关注与不断实践分不开的。换句话说,我们在讨论东汉晚期以来,早期中国时代的画像艺术对“空间”的表现上出现重大的视觉“变化”问题上,是不能够回避当时的士大夫画家阶层在理论构想与绘画实践上对其所造成的影响的。也许正是从东汉晚期开始,一些士大夫画家群体通过对塑造纵深“空间”这一重要议题的独特关注与实践,才使早期中国时期的画像艺术在对视觉“空间”的表现上,出现了一个较为深刻的视觉图式变化。认识到这一点,对于我们理解东汉晚期以来画像艺术中,对“空间”的塑造模式的“变化”问题应该具有一定的启发性意义。 而到了五代、北宋时期,伴随着荆浩、关仝、董源、巨然、范宽、李成、燕文贵、郭熙等一批出色艺术家的全面崛起,古代中国的画家群体对“空间”的视觉表现图式上,在两宋时代也逐步趋于最终的定型。比如,及至北宋中期,随着该时期以表现纵深“空间”效果的全景式山水画风格的全面成熟,由郭熙提出的那一著名的“三远”理论就是一个关于艺术家在那个时代,该如何完美地塑造纵深的“空间”而展开的成熟化的思辨性探讨。当然,由于本文讨论的中心主要是分析从先秦—隋唐时期古代中国画像艺术中对空间塑造的“变化”历程,以及在这一“变化”历程的背后所隐现的原因问题。同时,也基于考虑到从五代—北宋时期的画像材料是如此的丰富而又异常复杂,因此,如要对唐、宋以后画家群体对“空间”的塑造问题再加以更为深入的分析与解读,那或许就要笔者另外著文再作专门性讨论了。 注释: ①需要做重要补充的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艺术与考古学系的方闻教授在其著作:《心印——中国书画风格与结构分析研究》(Images of the Mind)一书中,已经对从隋唐—北宋时期的山水画家群体,如何一步步地通过艺术实践与理论构思,逐步完成对纵深式视觉“空间”的成功塑造进行了系统性的分析与深入阐释。参阅(美)方闻:《心印——中国书画风格与结构分析研究》(Images of the Mind),李维琨译,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21-82。 ②在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美术史系的巫鸿教授于1987年,在其完成并出版的哈佛大学美术史系博士学位论文中,在有效地复原了东汉晚期在山东嘉祥县兴建的武梁祠堂之结构、画像材料在祠堂内配置关系的基础上,综合运用考古学、历史学与艺术史的研究方法,对该祠堂空间内分布的诸多画像题材所表现出的以宇宙、天象、仙界、社会伦理道德等观念作为中心的信仰“空间”意识做了较为深入与系统的分析。但笔者在这里所讨论的“空间”与他的那一研究角度并不相同。有关他对此问题的深入讨论,参阅(美)巫鸿:《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The Wu Liang Shrine:The Ideology of Early Chinese Pictorial Art),柳扬、岑河译,北京:三联书店,2006:91-249。 ③需要再做补充说明的是,在杨仁恺主编的《中国书画鉴赏》一书中,作者即将这一卷轴画作品定为隋、唐初期,这同时也是目前学术界的普遍看法。参阅杨仁恺:《中国书画鉴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75。然而,傅熹年先生则根据《游春图》画面上三个细节要素:幞头、斗栱、鸱尾的描绘制度问题,认为此画像材料的绘制年代应该不会早于北宋。但张伯驹先生却对此观点进行了质疑。参阅傅熹年:《关于展子虔〈游春图〉年代的探讨》,《文物》,1978,(11):40-52。张伯驹:《关于展子虔〈游春图〉年代的一点浅见》,《文物》,1979(4):83-84。 【参考文献】 [1]于安澜.画论丛刊(上)[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60:23-36. [2]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95-118.136-145. [3]阮璞.画学丛证[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8:42-53. [4](美)巫鸿.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The Wu Liang Shrine: The Ideology of Early Chinese Pictorial Art)[M].柳扬,岑河译.北京:三联书店,2006:150. [5]刘敦愿.美术考古与古代文明[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7:37. [6](英)苏立文(Michael Sullivan).艺术中国(The Arts of China) [M].徐坚译.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6:88. [7]于安澜.画史丛书(第一辑)[M].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60. [8]俞剑华.中国古代画论类编(上)[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2000:581-582. [9]于安澜.画论丛刊(上)[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60:1. [10](唐)李延寿.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1106. [11]于安澜.画史丛书(第一辑)[M].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98. [12]于安澜.画品丛书[M].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2:29-43. (责任编辑:admin) |
